丹尼尔·P·富勒(Daniel P. Fuller)在《福音与律法:对比还是延续?》(Gospel and Law: Contrast or Continuum?)一书中的研究视角,从副标题《时代论与圣约神学的释经学》(The Hermeneutics of Dispensationalism and Covenant Theology)可以看出[1]。 在他1957年的博士论文《时代论的释经学》(The Hermeneutics of Dispensationalism)中,富勒从他所接受的一种圣约神学立场出发,对时代论(Dispensationalism)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时代论的标志性特征——即将以色列与教会在末世计划和命运上的分割——源于一种企图将新约与旧约隔离的愿望,以避免新约的恩典原则受到旧约中运作的律法(行为)原则的污染。在他目前的这本书中,他记述了时代论内部的一种转变,即关于旧约和新约中恩典与行为关系的观点逐渐接近他对圣约神学的理解。然而,他的主要目的在于记录自己思想上的转变:他现在认为,在上帝对人类的治理中,从未存在一个基于人类行为来继承国度的原则。因此,他目前的观点是,律法原则(以行为为基础来继承国度)并不存在于旧约之下,因此,无论是时代论还是圣约神学,试图以律法与福音的对比来解释旧约和新约的努力,都是完全错误的。
或许,如果富勒能够清晰地辨别并考虑到圣约神学传统中关于摩西体制(Mosaic economy)内部的恩典与行为原则结合的解释,他的思想就不会发生这种令人遗憾的转变。按照这一传统观点的正确理解,在旧约之下,一个具有预表性质的国度如同一个覆盖层,叠加在基石层上,这个基石层构成了所有救赎性施行阶段的连续性,并最终指向那永恒的原型国度。在这基石层面上,即个人通过基督进入永恒国度的层面,不论是旧约还是其他所有救赎性的圣约之中的继承国度原则,都是主权的救赎恩典原则。然而,在旧约特有的暂时性属地国度的管理中,这一预表层面是由行为原则所驱动的,因为以色列人对圣约规定的遵守被作为他们维持国度祝福的基础。[2]
如果富勒能够考虑到圣约神学的独特形式所提供的思路,他在处理《罗马书》10章和《加拉太书》3章等关键经文时,其释经可能性将被彻底改变。然而,事实上,他通过一套复杂而曲折的释经过程,得出了与这些经文教导完全相悖的结论,即摩西体制内并不存在行为原则的运作。显然,正是因为保罗认识到在旧约预表层面中存在这一行为原则,他才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种“律法”原则是否废除了早先的亚伯拉罕应许之约。而正是他认识到在摩西体制中,同时存在一个以恩典为原则的基础层面掌控着永恒国度,才使他确定,摩西之约并未废除上帝向亚伯拉罕所作的应许。
使徒保罗反复描绘的旧约与新约之间的对比,正是耶利米关于新约的著名预言(耶31:31-34)中所指出的行为与恩典的对比。先知将旧约定义为一个可以被破坏,而且实际也的确被破坏的约,并宣告新约将不同于旧约,新约不会被破坏。当然,也确实有个体在新约中表现为不忠,但耶利米所指的是整个国度本身。新约中永恒的原型国度,即在圣灵中有关上帝公义知识的国度,是基于基督的功德而获得的,因此,这个国度的实现是上帝对基督子民的恩典保证,是确定无疑的——上帝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念他们的过犯。
然而,在旧约中即刻呈现的预表性国度显然缺乏这种不可破坏的保证,因为这一国度曾多次被剥夺,最终不可挽回地被废除,其子民被驱逐至流亡之地。实际上,旧约的国度体制最终被上帝以毁灭性的约中咒诅彻底终结。在这里起作用的原则显然完全不同于上帝在基督里主权恩典的应许与信心原则。如果不承认旧约中行为原则的运行,就无法解释耶路撒冷的荒凉。正如摩西在旧约的宪章文件中所郑重警告的,以色列人在迦南的国度是否延续存活,是以其遵守圣约为条件的;若对圣约之主表现出集体的不忠,将导致整个国度灾难性的终结。
在旧约中,即便是属神的真儿女的经历,也体现了在预表层面上行为原则的运行。尽管基督的主权恩典保障了他们对永恒国度的继承权,但他们与大批背约之民一样,仍失去了对迦南的所有权。当主执行旧约的行为原则时,他将整个民族逐出迦南,驱逐至巴比伦,被称为“罗·阿米”(即“非我子民”)。
此外,当以色列民族仍在应许之地时,即便是真信徒,也可能因严重违反民事律法而丧失他在预表国度中的地位。从个人层面上,包括选民在内的全体以色列民,与整个民族历史相似,其在预表性国度中的存续以顺服为基础。即便他们对所应许的基督拥有信心,但如果未能满足行为条件,也无法阻止预表层面上祝福的失落。
我们必须得出结论,旧约与新约之间既存在连续性,也存在对比性。在永恒救赎和天国继承的层面上,二者在基督里都体现了主权救赎恩典的连续性。然而,二者之间的对比在于,旧约涉及一个次等的、预表性的领域,在其中引入了一种与恩典-应许-信心原则完全相反的原则。正因这一行为原则的存在,旧约是可以被破坏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旧约与新约形成了对比,而非连续关系,正如上帝的先知耶利米所宣告的那样(耶31:31-34)。
如果富勒的错误仅仅限于未能认识到旧约中的行为原则,那已然足够严重,因为这会导致对旧约本质和摩西律法功能的重大误解,更不用说对许多相关圣经经文的曲解了。然而,富勒对行为原则的否定远远超出了否认其在摩西之约中的存在。他的立场,如前所述,是认为律法,作为与福音对立的事物,从未存在于上帝与人之间的国度约定之中。事实上,他声称,即便是无罪之人,若认为自己的顺服能够作为继承国度的基础,这种想法也会堕入魔鬼般的骄傲。因此,富勒拒绝了圣约神学中亚当的行为之约(Covenant of Works)的概念,并因此必然否认了传统关于末后亚当基督的工作的功德性质。
由此可见,富勒的问题不仅仅是在某一救赎体制圣经神学重建中出现了小缺陷,而是其系统神学中的巨大错误,牵涉到上帝对其国度之圣约治理的整体理解。
在对传统律法与福音对比的激进攻击中,令人遗憾的是,富勒宣称自己得到了某些自称效忠于改革宗信条的神学家的支持,其中之一便是诺曼·谢泼德(Norman Shepherd)。谢泼德在其论述中提出,上帝的各圣约的特点是一种连续的治理原则,而不是行为与恩典的对比。他进一步强调所有这些圣约的统一性,无论是前救赎性(pre-redemptive)还是救赎性的,明确主张它们都同时具有要求和应许两个特点。由此,我们被带入了一个神学模糊不清的世界,在这里,诸如“应许”和“恩典”这样的基本术语不再具有常规的含义。至少,富勒认识到,随着这一激进的转变——否认功德行为的可能性——他已经放弃了圣约神学。
当探讨上帝与亚当及基督之间的圣约关系中的称义问题时,传统的行为原则的必要性就变得十分明确了。如果第一位亚当顺服地履行上帝与他所立圣约的条款,那么毫无疑问,他理应被他的主宣告为义。亚当的称义将以他的行为为基础,并且完全符合这些善行所应得的奖赏。上帝宣告亚当为义,将是一个纯粹的公义行为(act of justice)。事实上,任何其他判决都会构成不公义。将恩典的概念引入对这种靠行为称义的神学分析中,从而模糊其行为特质,是毫无根据的。实际上,这种做法本质上暗示了一个极其荒谬的观点,即上帝可能随意地像魔鬼一样行事,将善称为恶,将恶称为善。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然而,这显然正是富勒和谢泼德的神学所采取的做法。他们明确地否定了行为原则。此外,在他们所谓的前救赎性的约(pre-redemptive)与救赎性的约之间的统一性中,所有约都被描述为一种混合的“要求加应许”模式,而无论这一共同的特征“应许”(恩典?)到底是什么,它都必须既适用于顺服的亚当的称义,也适用于福音下信徒的称义。在这种体系中,亚当的称义不能仅仅是单纯的公义或行为的问题,而是恩典。这种观点否认了律法与福音的区分,取而代之的是某种形式的连续性,在其中上帝公义被淡化甚至丧失了。
在富勒和谢泼德的神学逻辑中,对行为原则的否定进一步延伸到了第二亚当。这一点可以从谢泼德提出的一个论点看出,他反对在圣约治理中承认行为原则。他指出,圣约关系本质上是父子关系,并据此得出结论:人从上帝这位天父那里得到的任何恩待,都是基于父爱的恩典,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义要求。然而,如果父子关系的存在排除了简单公义作为支配原则的可能性,那么同样,单纯的公义也不足以解释上帝对他的儿子、第二亚当顺服的回应,正如它无法解释上帝与第一亚当的关系一样。这意味着,在富勒-谢泼德神学中,耶稣基督所完成的顺服工作并没有使他配得来自天父的称义判决。第二亚当的称义因此并不是根据行为与恩典相对立的原则,而是基于某种包含恩典的原则来解释——由于基督的行为不足以满足公义要求所以这种恩典是必要的。
我们将在下文进一步反思这种否认基督工作完全功德的观点所带来的毁灭性影响,特别是在通过基督的义归算给信徒而实现的救赎性称义教义上的后果。
如果说,尽管有种种相反的迹象,富勒和谢泼德神学真的主张顺服的亚当的称义是基于行为而毫无恩典的掺杂,那他们对律法与福音之间对比的否定还是遇到困难。因为如果说在前救赎性的约(pre-redemptive)中的称义是通过行为实现的,同时又宣称所有圣约具有统一性(与传统观点相对立,传统观点认为前救赎之约和救赎之约是通过行为与恩典的对比来区分的),这就意味着福音之下信徒的称义也是通过他们的行为实现的。我们必须假设,富勒和谢泼德的神学并不想提出这种与福音如此明显对立的结论,福音说“主是我们的义”。因此,显然,这将富勒-谢泼德神学置于之前提到的另一困境中,即由于否认第一亚当和第二亚当通过行为称义而引发的困境。
反对在上帝的圣约中承认行为原则的立场,通常诉诸圣约守约者所获得祝福的伟大性。其论点是,这种奖励超越了单纯的公义,只能以恩典原则来解释。因此,有人声称,亚当若被确立在义的状态中,并被赋予那完全实现的国度中永恒安息的福乐,这必定是超越公义的事物,超出其顺服所应得的功德。基于这一观点的逻辑,必须进一步主张,这同样适用于第二亚当所获得的国度荣耀的奖励。然而,这种关于功德和公义的观念是臆测,而非基于圣经。这一观点可追溯到罗马天主教的一种抽象教义,该教义将“义理功德”(condign merit)与“情谊功德”(congruent merit)区分开来,并主张,人类唯有通过参与其关于人类存在的“自然-恩典”结构中的恩典层次,才能够配得永恒的益处的义理功德。讽刺的是,那些提倡这种方法的神学家,其观点显然在根本上受制于“自然-恩典”谬误,却自认为已经摆脱了改革宗神学中残留的经院哲学元素。
如果我们的神学真正以圣经为基础,我们就一定会坚持,任何仅仅属于人的义都不是一种自主的所有品或成就。然而,我们不会抽象地定义公义,而是根据上帝实际创造的现实以及圣经的启示来定义公义。我们会意识到,人类对荣耀状态的实现以及对安息日完全成就的盼望,是基于他作为按荣耀之神的形象被造之本性。这种期盼是与生俱来的,对完全的渴望是深深根植于人灵魂对上帝及其神性之追求中的。如果这种完全被否定,人就会在灵魂深处感到彻底的挫败。任何不及这种完全的恩赐都不是真正的祝福,而是一种咒诅。若给予他少于此的报酬,就是以恶报善,这并不是公义的回报。如果我们不是以臆测为基础,而是以上帝创造性结构的现实为依据来定义公义,那么我们将这样定义:如果人按照圣约条款行善而非作恶,那么按照圣约中的末世性制裁,公义意味着他从上帝那里得到的是善而非恶。而一套非推测性的圣经神学将把这样的圣约约定认定为基于行为的,而非恩典的。
根据上帝创造性秩序的安排,无论是在前救赎之约还是在救赎历史中,“他所称为义的人,他也叫他们得荣耀”(罗8:30)都是一种必要且不可避免的次序。在这司法与末世性结合的框架内,得荣耀与称义紧密绑定,并且得荣耀是称义的必然表现。一旦确定某一圣约中称义所依据的原则,该圣约中授予末世性祝福的原则也随之被确定。如果称义是以行为为基础并作为单纯公义的结果(如在前救赎之约中),那么荣耀就不会通过恩典实现。而如果称义是通过因信称义的恩典(如在福音之下),那么荣耀就不会通过行为实现。因此,在上帝对第一亚当以及第二亚当(在父与子之间的永恒之约中)的约定中,运行的原则是行为,而非恩典;上帝对顺服的回应是公义,仅此而已。若暗示上帝的奖赏可能少于应许的内容,就等于暗示上帝可能行不公之事。
假设富勒与谢泼德对行为原则的评估是正确的,那么耶稣在顺服地献上自己,以代赎受死的方式完成使命时的祷告就应该与事实大相径庭。根据他们的观点,耶稣的祷告大意应该是,虽然他并没有真正赢得与天父同在的荣耀的奖赏,但作为天父恩典的礼物,他还是渴望得到它。然而,我们的主实际所做的,是指出他顺服地完成了父安排的工作,构成了对奖赏的正当要求:”我已经荣耀了你……现在,父啊,求你荣耀我”(约翰福音 17:4-5)。按照富勒的说辞,耶稣祷告的精神是受魔鬼启发的。当然,作为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对自己的表述如此深恶痛绝,这样的暗示肯定会迫使富勒和谢泼德停下来,重新考虑他们放弃律法与福音的对比和拒绝行为原则的做法。
与上述问题密切相关,但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富勒和谢泼德的神学对改革宗正统的另一重大背离。随着他们否认行为原则,他们对圣约代表的试验(probation)和法理性归算(forensic imputation)这一基本神学构架进行了彻底修订。根据圣经的教导,两位亚当在试验性角色中都需要履行一种义的行为,这种行为将被归算到他们所代表之人的账上,成为称义和继承上帝国度的基础。这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将一种主观的义的状态从一人传递给多人,而是通过圣约代表的具体义的成就进行的法理性的归算。这试验的决定性成就包括履行一项特定的圣约行为,因此被描述为“一次的义行”(罗5:18)。在第二亚当的这一次的义行中,还额外包括了承担多人罪罚的被动顺服的维度。当我们认识到这一主动顺服的行为具有战斗胜利的特质时,它具体而统一的本质便更加清晰了。与撒旦的对峙是两位亚当试验危机中的关键所在。作为上帝的仆人,他们必须与上帝的敌人战斗,并以上帝的名义战胜敌人,这正是“一次的义行”所要求完成的圣约任务。这一次义的胜利由一人赢得,并归算给众人,作为他们的义行,并成为他们在圣约中获得所应许国度的合法权利依据。
刚刚描述的试验与归算教义,与否认人类行为作为神圣奖赏基础的立场显然互不相容。按照该立场(如我们之前已经观察到的),无论是亚当还是基督,在成功通过试验后所得到的称义宣告和圣约中应许的末世性祝福的赐予,都不再是单纯的公义(如传统改革宗神学所主张的),而是一种恩典。这种立场对福音理解的重大错误在于,如此一来,基督通过主动顺服所成就的功德便不再被视为归算给选民的基础,无法作为他们称义与继承国度的依据。事实上,在富勒-谢泼德的立场中,归算的合理性总体上变得模糊不清,甚至可能完全丧失,因为无论是第一亚当还是第二亚当,都没有成就任何义行作为被归算之人的称义和末世祝福的正当法理性基础。
因此,不出意料,在这种立场下,对称义教义中的法理性因素受到极少的关注。称义的消极层面可能会得到应有的表达,比如他们会承认基督承担了其子民罪的刑罚,从而为他们赢得了赦免。然而,基督的主动顺服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在谢泼德的教导中,人们常常在期望看到基督主动顺服的阐释时,反而发现其重点放在了与基督联合上。因此,我们得出这样的推测:在这种对称义教义的再定义中,重点在于众人经历了与基督的联合,从而有资格与基督一同蒙福。这种观点被用来取代传统法理观念,即基督一人决定性的功德行为被归算给众人,作为他们称义的基础。这种被修订的称义教义更接近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尽管这一解读可能会引发争议,但事实依然是,这些模糊表达的教导正在悲剧性地混淆教会对基督教信仰核心教义的理解。
最后,我们回到富勒的书作,这是我们正式讨论的起点。否认律法与福音的区分,将所有圣约——不仅是旧约和新约的救赎性圣约,还包括前救赎之约和救赎性圣约——统一起来,这种对圣约神学的修订,表面上似乎提供了对时代论最一致的回应,然而,这种形式上的表面优势实际上是虚幻的,因为它以违反圣经关于上帝圣约的核心教导为代价。由于在这些关键问题上的偏离,这种修订版的圣约神学本身必须被视为一种与富勒最初试图纠正的时代论同样严重的错误。
[1] 这些评论最初源自对富勒1980年出版的书的一篇(未发表)书评。为了增强其相关性,评论的视角已经扩大,涵盖了对诺曼·谢泼德当前颇具争议的教义的评估。谢泼德立场的根本特点,与富勒为其书标题问题所提供的“连续性”答案中所主张的相似,即同样抹去了圣经中律法(行为)与福音(恩典)之间的对立。本研究的当前修订版在某种程度上更进一步,转向对富勒-谢泼德神学的批判性分析。
[2] 关于这一观点的全面讨论,尤其是其在圣约神学历史中的地位,可参阅马克·W·卡尔伯格(Mark W. Karlberg)发表在《西敏神学期刊》(The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中的文章,第43卷第1期(1980年),第1-57页,以及第43卷第2期(1981年),第213-246页。这些文章还对富勒的书作出了尖锐的评论。
原著:Meredith G. Kline, “Of Works and Grace”, Presbyterion 9:1-2 (Spring/Fall 1983): 85-92.
译者:王一
作者:克莱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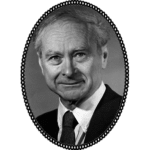 梅瑞狄斯·克莱恩博士(Dr. Meredith G. Kline, 1922-2007),生前为美国正统长老会按立牧师,著名旧约学者神学家。曾任教于费城威敏斯特神学院(1948-77)、戈登-康维尔神学院(1965–93)、改革宗神学院(1979–83)、加州威敏斯特神学院(1981–2002)等多所院校,他也同时是加州威敏斯特神学院和戈登-康维尔神学院的荣誉教授直至过世。
梅瑞狄斯·克莱恩博士(Dr. Meredith G. Kline, 1922-2007),生前为美国正统长老会按立牧师,著名旧约学者神学家。曾任教于费城威敏斯特神学院(1948-77)、戈登-康维尔神学院(1965–93)、改革宗神学院(1979–83)、加州威敏斯特神学院(1981–2002)等多所院校,他也同时是加州威敏斯特神学院和戈登-康维尔神学院的荣誉教授直至过世。
他曾于费城威敏斯特神学院获神学硕士(Th.M.),并于卓西大学(Dropsie University,1956)获亚述学研究与埃及学研究方向哲学博士(Ph.D. in Assyriology and Egyptology)。其著作有Treaty of the Great King: the Covenant Structure of Deuteronomy, Studies and Commentary; Kingdom Prologue; The Structure of Biblical Authority等。


2spm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