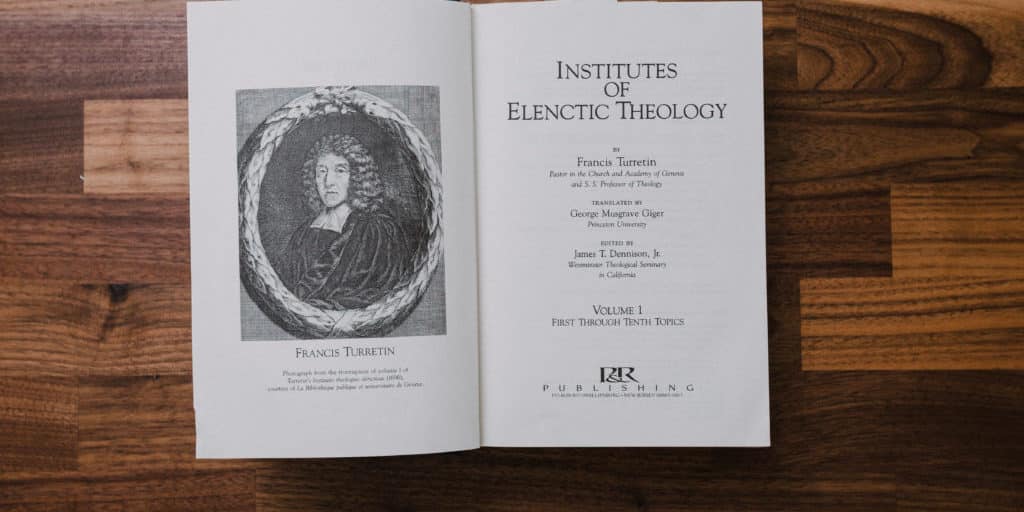第一要点:神学
第4问:自然神学是否足以使人得救?或者是否存在一种普遍宗教能使所有人都得救?我们否定这些观点,反对苏西尼派和抗辩派的立场。
问题的起因(occasio quaestionis)
一、伯拉纠派(Pelagians)的不敬虔教义认为,任何宗教中根基稳固的人都能得救,这引发了本问题。不仅自由派(Libertines)、大卫·约里斯派(David-Jorists)等(他们满足于诚实文明的生活,认为宗教无关紧要)持此观点,当今的苏西尼派(Socinians)也明确赞同。他们一方面直接教导说,那些按照自然之光敬拜上帝的人(将这光视为某种更隐秘的道)能讨神喜悦并得赏赐(参见苏西尼《神学讲义》第二卷;Socinus, Praelectiones theologica 2 [1627], pp. 3–7);另一方面又间接地减少救赎所绝对必需的宗教教义数量,并认为所有人都能以相同方式和程度接受这些教义。抗辩派(Remonstrants)显然也持相同立场:有些人如库尔塞留(Curcellaeus)和阿道夫·维纳托(Adolphus Venator)在《驳多特牧师书》(Een besonder Tractaet … der Predicanten der Stadt Dordrecht [1612])中公开否认”凡不以真信心与基督联合的人都不能得救”这一命题;另一些人如亚米纽斯(Arminius)、科尔维努(Corvinus)、伊皮斯科皮乌(Episcopius)则较为谨慎,他们不是直接而是间接的认为,外邦人和其他人通过正确运用自然之光可以获得恩典之光,并藉此进入荣耀(Arminius, “The Apology or Defence of James Arminius Against Certain Theological Articles,” 15, 16, 17 in The Writings of James Arminius [1956], 1:322–29; and Arnoldus [Johannes Arnoldus Corvinus], Defensio sententiae … I. Arminii [1613] against Tilenus)。许多罗马天主教徒也持同样错误观点,如阿布伦西斯(Abulensis)、杜兰杜斯(Durandus)、卡普雷奥鲁斯(Capreolus)、安德拉迪乌斯(Andradius)、维加(Vega)、索托(Soto)、伊拉斯谟(Erasmus)等,他们都主张非基督徒即使不认识基督也能得救。
二、与之相反,正统神学家始终持守:人堕落之后,能带来救恩的真神学或真宗教唯有一种,即律法与福音圣言所启示的;除此之外的一切宗教,非属亵渎偶像崇拜,即为虚妄错谬。这些虚假错谬的宗教虽或保留了些许关于律法及对上帝认知(tou gnōstou Theou)的模糊残缺观念,但其功用不过使人无可推诿(anapologēton)而已。
三、问题关键不在于”宗教的某些首要原理(certain first principles)是否为众人所共有”。我们承认在自然神学中,藉着自然之光确实存在这类原理(例如神的存在、人应当敬拜神等),超自然神学正是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真正的问题在于:”真宗教所特有的完备的首要原理是否为所有人所掌握?”对此我们予以否定。
问题的界定(status quaestionis)
四、我们讨论的重点,并非质疑自然神学对人类的价值——我们完全承认它具有多重功用:(1)作为神向罪人施恩的见证,即便这些罪人根本不配领受这残存的光照(使徒行传14:16-17;约翰福音1:5);(2)作为维系人类社会外在规范的纽带,防止世界陷入彻底的败坏(罗马书2:14-15);(3)作为人领受恩典之光的主观条件,因为神启示的对象不是牲畜木石,而是理性的受造物;(4)激励人们寻求更清晰的启示(使徒行传14:27);(5)使人在今生因良心的控告(罗马书2:15)、在来世因神对人隐秘事的审判(罗马书2:16)而无可推诿(罗马书1:20)。
问题的实质在于:自然神学本身是否足以带来救恩?神赐下这种启示的目的,是否要让领受者借此得救?对此我们予以否定。
论证自然神学不足以使人得救
五、理由如下:(1)没有基督和对祂的信心,就不可能存在得救的宗教(约3:16;17:3;徒4:11-12;林前3:11;来11:6)。但基督唯独在福音中被启示,信心也唯有通过圣道才能产生,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罗10:17)。有人辩称这只是说明基督教是得救的常规途径,并不排除神能特例拯救那些按自然律法圣洁生活却不认识基督的人——这种观点站不住脚。既然圣经明证基督是得救的唯一道路(”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设想一条不藉着基督的特例途径实属僭越。(2)外邦人和一切缺乏基督圣道之人的境况,被称为”蒙昧无知的时候”(徒17:30),那时神”任凭万国各行其道”(徒14:16),他们敬拜”未识之神”(徒17:23),是”没有神”(弗2:12)的——若自然启示足以使人得救,就不会有此描述。(3)若普遍宗教能使人得救,福音和圣道宣讲就无必要。但保罗见证:”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林前1:21)。
解答的根据(fontes solutionum)
六、对神作为创造者与护理者具有一些不完全、败坏且模糊的认识是一回事;对神作为救赎者及敬拜对象具有完备、清晰认知则是另一回事。自然神学仅能提供前者,即对神的一般性认识(gnōstō tou Theou);唯有启示才能带来后者,即藉着圣道产生的真信心(tō pistō)。即便神在自然界中通过赐人物质恩惠(ta biotika,徒14:17)为自己显出证据(amartyron)——这些恩惠祂甚至常赐给那些祂所憎恶并定意毁灭之人——也不能因此推论外在呼召在客观上足以使人得救。因为经上明言神”任凭万国各行其道”(徒14:16),并称那时期为”蒙昧无知的时候”(徒17:30)——这显然是指外在呼召的缺陷,因使徒将之与新约时代对比,那时神藉圣道呼召人悔改。
七、基于神在基督里应许的启示,寻求祂的恩惠与恩典是一回事;通过观察自然与护理之工,来摸索那位”未识之神”,希望或许能寻见祂(使徒行传17:26-27)。后者确实适用于外邦人,但前者不适用。虽然圣经其他地方说”寻求神”(seek, quaerere)是指投靠祂的信实、寻求祂恩典的庇护,”寻见神”(find, invenire)是指得到所寻求的保护、并经历祂神圣本体的恩临,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处也要这样理解。因为两者寻求的对象和方式都明显不同。其他经文是指神立约的子民,而这里仅指与应许之约无关的外邦人。前者是通过神的话语认识神并弃绝偶像的人,后者是拜偶像却不认识神的人。前者是通过基督来寻求并认识那位施恩的神,后者是通过自然和护理之工来寻求那位未知的神,为要认识祂并与偶像区分。最后,前者直接明确地教导信徒应当寻求神,为着拯救而寻见祂;而这里则说,神在创造和管理世界时已经显明祂的能力和神性,为要引导人这样来寻求万物的创造主(即通过”摸索”来寻见祂)。没有人会说这也适用于旧约中那些圣徒,因为他们向来都是依靠神在基督里确切的应许来亲近神的。
八、罗马书1:19-20(论及人对神的可知之事,gnōstō tou Theou)并不支持存在一种能使所有人得救的普世宗教。(1)这段经文仅论及”可知之事”(gnōstō),而非”当信之事”(pistō)——后者才是使人得救的。(2)保罗说神的事”已经显明”(to gnōston)在外邦人中,但并非”全部知识”(pan gnōston),即仅指从自然之书可获知的,而非从神的话语中认识、且为得救必须知晓的(如三位一体的奥秘、基督救赎之功等)。(3)这种知识(gnōston)被使徒限定于神的”神性和大能”——即从创造与护理之工中可感知的神之存在与属性——通常归入自然神学范畴;但绝不包含对神在基督里旨意与恩慈的认识,这唯独来自祂的话语,绝非从其作为可得,而离此则无救恩可言。(4)这种知识(gnōston)仅足以使人无可推诿(罗1:20)。”以致”(eis to)一词不仅指偶然结果,更含神定旨之意——因这结果必是神借其谕令所成就之工的预定目的,而非仅凭律法要求的附带效应。
九、足以使人无可推诿的,并不因此就足以使人得救。因为要获得救恩所需的条件,远比招致公义审判而无可推诿(anapologētōs)所需的条件更多。因为罪恶源于某些缺陷,而良善则需要完整的成因。正如人在一点上跌倒,就是犯了全部的律法(雅各书2:10);但不能反过来说,人在一点上做得好,就在所有方面都算为义。犯一条罪就足以使人无可推诿,但行一件善事却不足以使人得救。因此,外邦人之所以无可推诿,是因为他们以无数假神取代了那位他们本可从自然之光中认识的独一真神;但我们不能由此推论,仅仅认识独一神就绝对足以使人得救。这种无可推诿的状态必须限于使徒所讨论的主题范围(即偶像崇拜),这足以定他们的罪,但即使避免了偶像崇拜,也不足以使他们得救。
十、人”可被免责”与”可得救赎”是两回事。即便外邦人能正确运用自然之光(这实际上不可能),他们也只能在某部分而非全部罪责上获得开脱。纵使他们能约束外在行为、避免后续犯罪,仍无法获得先前所犯之罪——尤其是原罪——的赦免,也无法改变其败坏的处境与本性。因他们所行之善仅是外在的、实质上的善,而非方式与源头上的善(因缺乏圣灵内住);即便有益,也仅关乎现世或未来,却无法消除过往罪咎(而离此则无人能得救)。
十一、有人谬称在”神可知之事”(gnōstō tou Theou)中,客观上已存在恩典启示与救赎主的暗示——纵使不够清晰明确,至少是隐晦含蓄的,因人在其中可认知神为慈爱者,故在某种程度上(虽混乱模糊)也能视祂为接受赎价、呼召悔改并应许赦罪的救主。实则:首先,藉普遍性怜悯(仅关乎暂世福乐与刑罚延迟)认知神为怜悯者,与藉基督完成代赎所带来的特殊救赎性怜悯而认知祂截然不同;认识到神是可被安抚的、仁慈的,与确知神已经息怒或必将息怒,二者截然不同。我们承认,外邦人或许能通过自然之光认识到神是可被安抚的,却绝无可能确知神已经或必将息怒——而这正是安抚良心所必需的。若仅知神可被安抚,却不清楚祂是否愿意息怒、以及如何平息其忿怒,这认知有何益处呢?当人的良心因罪疚感和对神公义的畏惧而沉重时,唯有同时确知神的善意和满足其公义的方式,才能真正获得平安。然而,谁能否认这种完整的认识只能来自福音的真道——那向我们显明神在基督里恩慈的启示?若如某些人所言,外邦人始终以某种方式处于恩典之约下,并对基督救赎之恩怀有(虽模糊含蓄的)认知,那么保罗为何称这救恩是”永古隐藏的奥秘”(罗马书16:25)?又为何断言外邦人”与约无分、没有基督”(以弗所书2:12)?
十二、那些试图通过区分”直接充足性”(immediate sufficiency)与”间接充足性”(mediate sufficiency)来自圆其说的人,同样陷入困境。他们声称,外邦人虽不能获得直接充足的启示,却可能拥有间接充足的启示——因为假设若有人善用自然之光,神就必加赐恩典之光(他们认为这既符合神的怜悯,又可从基督”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太13:12)的教导中推知)。然而这种观点存在双重谬误:首先,将需要额外补充的启示称为”充足”是荒谬的(我们同样驳斥罗马天主教徒所谓”圣经间接充足论”,即认为圣经虽未包含全部真理,却指引我们通过传统获得);其次,他们未经证明就预设了结论——仿佛神有义务向善用自然之光者施恩,或这种关联能得到圣经支持。这观点显然源自伯拉纠主义”神必不拒绝尽力者之恩典”的谬误。太13:12在此根本不适用,因为该经文论及神以新的恩赐坚固已有的恩典性的恩赐,与自然性的恩赐毫无关系。
十三、罗马书2:4(”神的恩慈是领你悔改” to chrēston tou Theou eis metanoian agein)不适用于此议题,因为保罗此处论述的对象并非外邦人,而是犹太人——他在本章旨在定犹太人的罪,正如第一章已证明外邦人有罪。这从以下两点可知:(1)他所描述的受话者特征唯犹太人特有,如”你论断行同样事的人”等;(2)第17节明确以”你称为犹太人”指名对话对象。该节并非转向新对象的论述开端,而是前文对话的延续,只是更清晰地指明了对象。因此,这里所说的”恩慈”(chrēstotēs)特指赐予犹太人的启示与恩惠,与普遍护理之工无关。
十四、虽然外邦人的良心有时可为他们辩解(罗2:14-15),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此状态下能获得真实稳固的平安及随之而来的完全救恩。良心在某些事上或部分地为人的辩护是一回事——这确实存在;在所有事上或全部地为人的开脱是另一回事——这绝无可能。同样,将人从较严重的罪行中(相对于更邪恶的行为)辩解出来是一回事,而赐予我们那种从感受神的爱及与祂和好而来的确定、持久的平安则是另一回事——这是外邦人所不具备的。
十五、必须区分律法的设定状态(status instituti)与失效状态(status destituti)。前者指律法就其本质而言的状态——在人类堕落之前,律法被赐予是为使人得生命,其本身也确实导向生命,正如”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参罗2:13)的规定所示;后者则指律法与我们关系中的状态——堕落之后,人因肉体的软弱而无力遵行,此时律法被赐下不再是为赐予生命,而是作为显明罪恶与悲惨的镜子,使罪人无可推诿(罗3:19-20)。
十六、”律法的功用”可从两方面理解:或指律法本身的功能(形式层面),或指律法对人的要求(命令层面)。前者是律法对人产生的工作或者说责任,包括教导、应许、禁止和警告;后者则是人对律法的遵守的工作。外邦人”行律法上的事”(罗2:14)并非指后者(即遵行律法要求),而是指前者——他们所做的与律法本身的功能一致,即规定善行、禁止恶事。这显明于:(1) 保罗的整体论证目的是要证明外邦人即使没有成文律法,也因自然律而面临死亡;(2) 后续解释性经文(exēgētika)表明”没有律法的人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故”行律法上的事”等同于”以自己为律法”。
十七、虽然某些外邦人(相对而言)可能比其他人更好;尽管他们的行为从世俗角度可称为美德,并因此获得规范生活的双重回报——既有现世利益和良心平安等积极回报,也能使惩罚相对减轻——然而在神眼中,他们最好的行为不过是更华丽的罪,根本不配得任何奖赏。
十八、此处引用的麦基洗德、约伯、百夫长等例证均不适用,因他们被圣经称赞的作为皆得益于特殊恩典与启示的辅助,而非仅凭自然之光。
十九、哥尼流(Cornelius)虽生为外邦人,实为宗教上的皈依者(proselyte)。他虽未能相信弥赛亚已降临且就是彼得所传的耶稣,却能与犹太人一样凭先知预言相信弥赛亚必将降临。因此他当归类于期盼未显明之救主的先祖之列,而非外邦人。故彼得到来时,他所获得的并非信心的开端,而是信心的增长。
二十、希伯来书11:6所提到的两个点(”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祂赏赐那寻求祂的人”)不可仅从物理层面理解(仿佛凭理性之光就能认知),而应从超物理与神学角度理解——这指向救赎性认知向我们显明的真理:不仅确信神的存在及其作为万有全能创造者的身份,更认识祂的本质(圣父、圣子、圣灵),以及在人类堕落之后,祂是救赎主,不仅赏赐那些凭行为律法性寻求祂的人,更赏赐那些藉恩典、通过对中保的信心以福音方式寻求祂的人。以下论证表明这正是使徒的原意:(1)贯穿全章论述的”得救的信心”这一属性;(2)所列举圣徒的例证表明,使徒所言”信神”绝非对神普遍恩慈的泛泛认知,而是对这位因基督赐下天上福分的真神的认识。使徒所言”到神面前来”特指在基督里与神相交(参希伯来书4:16;7:25;10:22等处)。因此,库尔塞留(Curcellaeus)将”信神”与”信基督”割裂是谬误的——他将前者视为得救绝对必需,后者则仅在神圣启示后才需要。事实上,凡不与”信基督”相连的”信神”皆非真实有效的得救之信(约14:1),因我们唯有通过基督才能信神。
二十一、我们并不否认某些教父曾对按理性生活的外邦人和哲学家抱有得救的期望(如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在《杂文集》Clement of Alexandria, Stromata, 6.5,17 中的论述;殉道者查士丁在《第一护教辞》Justin Martyr, First Apology, 46中的观点;约翰·克里索斯托在《马太福音讲道集》第36[37]篇的见解John Chrysostom, “Sermon 36 [37],” Homilies on the Gospel of Matthew,以及艾萨克·卡索邦在《论神圣事物》Isaac Casaubon, De rebus sacris et … exercitationes … Baronii 1* [1614], pp. 2– 4 中引述的其他例证)。然而,在伯拉纠主义兴起前,这些尚能谨慎表达的观点固然情有可原;但在奥古斯丁及其追随者极力捍卫”唯有藉基督恩典得救”的教义后,许多经院学者(Scholastics)仍重蹈覆辙,这就更令人诧异了。
二十二、茨温利(Zwingli)曾将赫拉克勒斯(Hercules)、忒修斯(Theseus)、努马(Numa)、阿里斯提德(Aristides)、苏格拉底(Socrates)等杰出人物列入天国(《基督教信仰简释》第12章,A Short and Clear Exposition of the Christian Faith, 12)。在描述天家圣众时,他除提及新旧约圣徒外,更写道:”在那里你将见到赫拉克勒斯、忒修斯、苏格拉底、阿里斯提德、努马等人;在那里你将遇见凭信心离世的列祖。”此举虽非我们所赞同,但需明辨其谬误实质:他并非主张救恩之门可脱离基督与信心而开,而是揣测神圣怜悯或许(以人不可知的方式)在那些被赋予英雄美德者心中植入了信心。这从他明确论及”凭信心离世”可见——此语不仅指君王的先祖,更涵盖前述所有贤哲。其在《致乌尔班·瑞吉乌斯论原罪》(De peccato originali declaratio, ad Urbanum Rhegium [1526], CR 92.379)中的声明可佐证此意:”那些判定所有外邦人灭亡的人实属谬误,谁又能测度神之手在每人心中书写了多少信心?”
二十三、外邦人的各种献祭并不能证明他们认识神在基督里的恩慈。这些祭物并非为求取祂的救赎之恩(这恩典若非启示便无从知晓,因其施行全然出于神的主权),而更多是为平息祂的公义(这公义凭自然即可认知,且其施行乃必然之事)。
本文翻译自 Francis Turretin, Institutes of Elenctic Theology, 3 vols., trans. by George Musgrave Giger, ed. by James T. Dennison, Jr. (P&R, 1992-97). 部分按照拉丁原版修订。
改革宗初学者将逐步连载这部重要的改革宗正统派神学作品。
作者:图伦庭